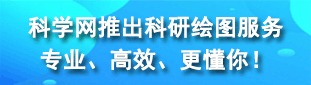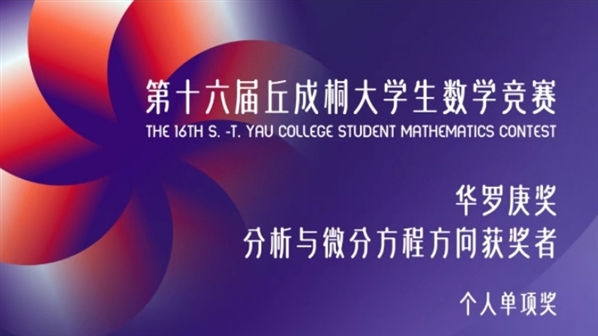没写毕业论文,他们却成了“优秀”
天津大学工程硕士研究生冯丽艳的工作是在她的毕业“答辩”现场找到的。“找工作”的过程很简单——正在她介绍自己的研究时,现场的一位企业总工程师忽然说:“你工作做得这么好,来我们这儿上班吧。”
打动这位总工的并不是冯丽艳的论文有多出色。事实上,那天冯丽艳讲解的并不是她的毕业论文,而是一项科研成果。这场“答辩”也不普通,它有一个正式名称——天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实践成果鉴定会。
这样的“鉴定会”,天津大学今年一共举办了10场。包括冯丽艳在内的10名工程硕士研究生凭借自己的实践成果,不但拿到了学位,还获得了学校颁发的优秀实践成果证书。他们也成为国内高校中,首批通过实践成果获得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
给以后的学生“打个样儿”
冯丽艳的成果针对自来水厂在水处理的混凝阶段,相关药剂添加量不精确的问题。该成果利用人工智能的自动学习机制和可解释分析能力,实现了药量的精准投加,从而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该项目来自冯丽艳导师的一个横向课题。冯丽艳自2023年6月接手该项目,于2024年12月完成并通过企业验收。此后,冯丽艳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毕业论文的写作上。
然而在今年4月,学校的一纸通知却改变了冯丽艳的毕业“节奏”——天津大学允许工程类硕士毕业生凭借实践成果参加毕业答辩,通过答辩者便可以获得硕士学位。通知还鼓励有类似成果的学生积极报名。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我们一时兴起,而是基于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刘庆岭说。
据他介绍,早在2023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分类培养的指导文件,乃至今年年初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中,都明确规定研究生可以“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申请学位。
“2024年,天津大学受教育部相关部门委托,起草工程类硕士生按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具体方案和形式。”刘庆岭说,最终他们将形式确定为5类,除了专题研究类论文外,还包括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形式。方案交付教育部后,得到了相关部门认可。
接下来,便是实践了。
今年4月,天津大学决定在今年毕业的工程类硕士研究生中,率先开展凭借实践成果颁发学位的尝试,这也就有了改变冯丽艳毕业节奏的那则通知。
“最终,全校共有近20名工程类研究生报名,我们在其中选择了10名。”刘庆岭说,“我们希望将他们作为一个‘样本’,给以后的学生们‘打个样儿’。”
“你们这样培养,企业就不用入职后再培养了”
之所以能成为“样本”,是因为这些学生的实践项目的确“够硬”。
“我们选择的这些学生来自包括环境学院、建工学院、材料学院等在内的不同学院,其成果包括不同形式。”刘庆岭告诉《中国科学报》,尽管这些成果各不相同,但均有很强的工程实践价值及很高的技术水准。
按照天津大学的规定,此次参评的实践成果首先要经过专家鉴定,同时要求参与鉴定的校内外专家中,来自企业以及行业领域的专家不少于一半。只有获得了这些专家的肯定,项目才能申请进入答辩程序。
作为首个通过鉴定的成果,该校工程硕士研究生钟行建的方案设计直指航空航天领域。“我的方案通过融合飞机蒙皮智能数据获取与缺陷检测算法,为飞机保养维修保证航线安全提供数智赋能。”钟行建如此介绍自己的方案。经答辩与技术论证,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方案工程价值突出,具备良好应用前景。
该校硕士研究生邹豪坤研发的“激光测距仿真设备”也让鉴定会的专家眼前一亮。“这一设备对提高激光测距系统研发效率具有现实意义。”他介绍说。
该校硕士研究生李闯则聚焦海洋平台焊接痛点,提出一种基于主被动视觉传感器的解决方案。该成果已申请发明专利,并在焊接领域重要期刊发表文章……
面对这样的实践成果,以及能够做出这种成果的学生,最高兴的是那些来自企业界的评审专家。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徐德刚是其中一位参评学生的导师。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虽然在鉴定过程中,企业专家给学生的课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但更多是表达一种肯定和欣喜。
“学生的答辩结束后,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的某位企业界人士兴奋地告诉我,‘你们如果这样培养学生的话,我们企业就不用等他们入职后再培养了’。”徐德刚说。
理想状态:论文占比不超一半
一个看似只是毕业评价方式的变化,实际上牵动着整个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链条。
“当前,国内高校在工程类硕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学生们做的很多研究直接来自导师的课题,特别是一些横向类课题。”刘庆岭表示,国家之所以大力倡导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希望此类研究生能够直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实打实给出解决方案。“工程硕士在实践类课题方面的参与,正契合了国家的初衷。”
然而,此前工程类研究生仍需通过论文形式获取学位。这使得无论导师还是学生,在聚焦工程实践的同时,不得不兼顾论文撰写。
“很多实践类项目,是难以用论文形式呈现的。”刘庆岭打了个比方,这就像一个学徒花几年时间钻研包子馅的调制方法,但最终能否出师的标准,却不是他调的馅是否好吃,而是他能否写出一篇关于包子馅化学成分的研究论文。
“这是一种明显的错位。”刘庆岭说,正是这种错位使很多导师难以让学生专注于实践项目的研究。
对此,身为导师的徐德刚深以为然。
“在如今的智能时代,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已经从早期的知识传授过渡到对学生能力以及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一点对于工程类研究生的培养尤其重要。”他举例说,实际的工程应用领域非常注重研究人员的“节点”意识,以及思维的严谨性和系统性,但这些在传统的高校教育体系中涉及并不多。
“真正锻炼这种能力的地方就是工程实践现场,但由于学生的毕业标准只是论文,而不是实践成果,导致很多导师即便有意让学生深入实践,也不得不考虑学生的‘毕业问题’。”徐德刚说。
然而,如果工程类硕士的毕业评价标准以及形式变得多样,情况便大为不同。
在刘庆岭的设想中,如果今年的探索能在未来全面推广,工程类硕士毕业考评中“论文”的占比将降至50%以下,其余学生则可以凭借实践成果——方案、图纸、产品等,获得学位证书。“这应该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他说。
在今年天津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冯丽艳与其他9名研究生成为第一批上台接受学位证书的学生。同时,他们还获得了学校颁发的优秀实践成果证书。台下掌声响起的那一刻,刘庆岭坚信,“未来,能够收获这样掌声的天津大学学子一定会越来越多”。
| 分享1 |